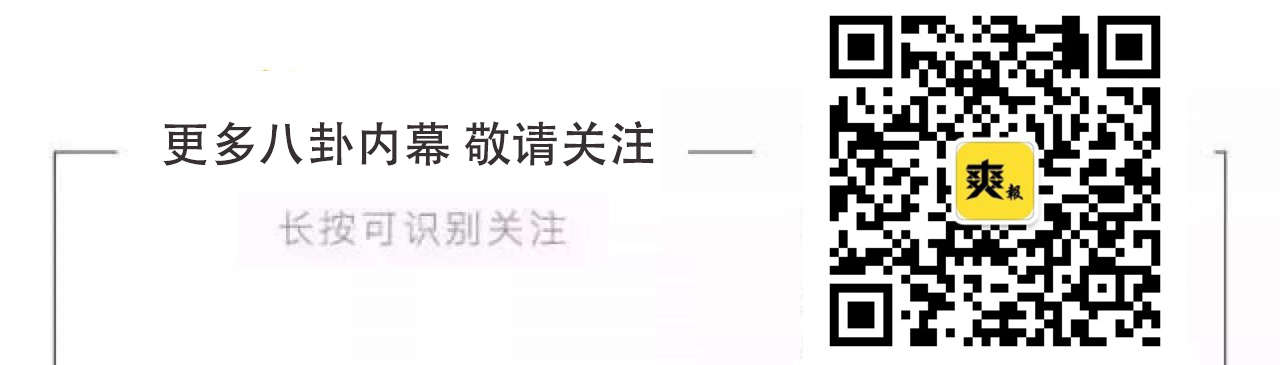从没想过这一拍,拍了二十年。这么长的时间足可作一部大历史的统整追叙,或一段可歌可泣的抗争纪实。但黄惠侦的镜头始终平静。视线在外头绕一圈,最后还是回到那个家。
家是什么?是昏暗老房和牵亡现场,两点一线的每日来回。十岁时妈妈带她和妹妹逃离家暴的父亲,为了生计,她国小三年级后就离开学校,随妈妈一起投入阵头工作,对未来的想像只有“长大后就去歌仔戏班,或当乐师,薪水又好又轻松”。日子苦不打紧,但某次长辈随口直说妈妈“喜欢查某人,是变态”的一句话,却彻底颠覆她的世界。
单亲,牵亡人员,女同志母亲,辍学小孩。深具边缘象征的词汇贴满她的家庭。直到20岁那年杨力州替公视制作影片,前来采访牵亡现场,她才认识什么是纪录片。“这社会看待你就是不一样,但他们不认识我,为何可以把我讲成就是那个样子?”恰逢当时摄影机已经相当普及,她开始去社区大学上课,尝试拍摄自己的家庭,“透过这台小小的机器,可以讲讲我是谁,拥有自己的诠释权。”
重拾摄影机,为圆满一段关系而拍
纪录就这样断断续续展开。但妈妈在家里是沉默的。很长一段时间黄惠侦怀疑母亲其实不爱她,不然怎会和她无话可说,到外头却变一个人,欢颜畅谈,结识好几任女友,甚至花大钱在她们身上?虽然始终住一起,母女犹如各站天秤一端,只能勉强维持平衡。直到黄惠侦自己有了女儿。看着懵懂的女儿一点点长大,她忽然惊觉岁月其实不停流逝,她变老,母亲更老,彼此还剩多少时间?
“20岁时,我还在找自己是谁,所以很在意社会给的标签。可是后来已经知道自己是谁,标签不再是困扰。即便动机不同,还是想把这部片完成。那对我的意义比较大。”直到此刻,黄惠侦才换上导演视角,准备说一个完整故事。恰逢2012年底多元家庭民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,同志议题再度浮上台面,她发现这部片的另一层意义:说出她们的日常,分享给更多关心或对同志陌生的大众。
能说出口的,就不再是问题
从年轻时憎恨母亲的冷淡,后来同理为人母的难处,最后反过来展开属于两人的对话。开口是最难的,片中经常看见妈妈挥手说“不要再讲了”。但黄惠侦认为,就算过去的事情已成定局,只要说出来,都会有改变。最长的一幕,两人在餐厅各据一方,道出多年前的心结,语毕妈妈离席,摄影机还在录,而她一人坐在桌边不停哭泣。“拍这部片改变最大的是我。”她说,“过去我们都各筑一道墙,讲开来才发现,啊,其实都没必要。”
为了分别在电视台和戏院播映,黄惠侦剪了54分钟的《我和我的T妈妈》与89分钟的《日常对话》两种版本,前者以牵亡贯串,尚带点激动的情绪,后者则更完整呈现包括母亲、舅父、女友们、妹妹、侄女等家人们的访问,平实而饱满。最后一段幼小的女儿撒娇问黄惠侦的母亲爱不爱她,母亲回“我嘛爱你”,像替多年的冷战划下句点。电影不但夺下今年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,许多观众也给予温暖的回馈,让母亲和家族长辈更正面看待过去不敢言说的同志话题。
“我们”活在同一个时代
虽然讲的是私人经历,却可能和很多人的生命经验重叠。黄惠侦过去在劳工协会和中国时报工会工作的历练告诉她,每个人的遭遇都是大环境的缩影。她的镜头接下来要转向三莺部落,观看这一群从乡下来都市讨生活,却连房子都租不起,最后长期寄居于桥下的原住民。“但不管拍什么,最后还是回到人本身。我们其实没有相去太远,甚至在面临一样的问题。所以不管主题是原住民或移工,我都觉得是在拍一个‘我们’的故事。”她说。不分文化、阶级,人类的情感终究相通,镜头内如此,镜头外更是。
Info│黄惠侦 曾任职于台湾国际劳工协会,中国时报产业工会,以及台北纪录片工会暨秘书长。创作主题以社会关怀为主。2016年的作品《日常对话》,获金马奖提名,并夺下柏林影展中锁定LGBT题材的泰迪熊奖之最佳纪录片。